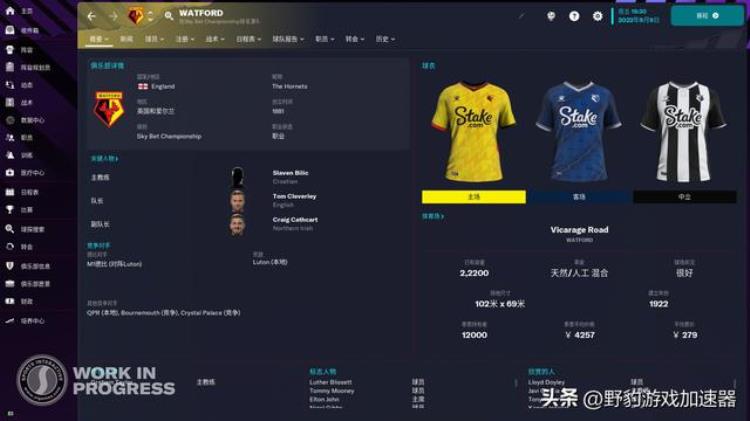我的爷爷云山
我 的 爷 爷
作者:云山
我的爷爷穿光板子老羊皮袄,戴狗皮帽子,帽耳刮子耷拉耷拉地摆,筒着双手抱个拾粪叉子,背个烂茬茬背篼……

一
日头在梁畔上烧。
灰蓝里透着白的天。一绺死云,懒汉般荡过了梁上的峁疙瘩。六月六都过了,老天爷连一点子雨星子还没挤下来。
没有风。七八只红嘴鸦儿,扑扇着铁黑的翅子,从涧沟纵横的崖畔上掠过。“啾喂!嘎——”“啾喂!嘎——”的叫声,此起彼伏,平平仄仄,在沟脑里荡漾。发烧的土地便有些莫名的凄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定西部山区。光阴就这样驴不卸鞍骡不歇蹄地在乌鸦麻雀的呱躁声里恍恍惚惚漫不经心地走。
阳洼里的婆娘们天麻麻亮就到屲上铲草皮挖蒿根去了。庄农人没庄稼,不要说人吃的,驴槽里添的,灶头里烧的,炕洞里捣的,都没了。从惊蛰到入伏,阳婆就这么劈头盖脸面红耳赤地晒,犁地的家当像月婆子一样,窝在草棚里破窑里缓着。
窖里的水老早刮干了。清明前后,各家窖底子里还有点泥巴糊糊。庄子上手脚不干净的人便三更半夜起来偷窖里的水,家家窖口上便多了一把锁。锁子锁君子锁不住小人,贼娃子照偷不误。庄农人没坛场,抓不了贼但做贼麻利,一庄人便你偷我我偷你,把水从这眼水窖里倒到那眼水窖里。水没见多,偷去偷来倒浪费了不少,好歹是户户没水吃。
涧沟里有泉,但蚀人蚀人地又咸又苦,牛羊舔都不舔。爷死死拽着羊耳朵摁着这些畜生喝,直喝得毛色都变了,焦毛骸糙地刺猬般炸着。
快饭罢了。红日头滚过了榆树稍,猫眼仁子变成了一条绣花线,拾柴担水的人还没到屋里。
爷揽了一背篼干驴粪,剁几个麻洋芋,吭啷啷烧开半锅水,和着糜面薯干面苞谷面搅和着,待到这些杂粮面糊糊渐渐凝固,在馓饭叉子上能吊住线的时候,灰暗狭窄的厨房里便有了焦锅巴的香味。
庄外场沿上,卧个青石头碌碡。爷和我,端一大一小蓝边碗馓饭,蹲在碌碡上扑腾腾吃。
搅团馓饭,老汉娃娃的好饭。爷几下就刨完了饭。爷单手托碗,拇指紧抵碗底,其余四指扣住碗帮,虎口间隙,圆如马镫。爷运腕自如,深入浅出,五指或钩或捺,或送或拨,或提或顿,碗捻线杆子般飞快的旋。勾头,展舌,拉下颌,一气呵成,糊在碗里的馓饭被舌头风一般卷进了咽眼子。爷舌头由碗边朝碗底,扫场耱地一样一茬压一茬地掠过去,碗底便清水洗过一样不留半点馓饭,光鲜如新,端地像狗舔过一样了。爷伸长舌头,在嘴的上下左右扫几圈,舀半马勺生浆水,咣咚咣咚灌下去,双手在嘴上和胡子上两抹一捋,两个结满老茧的掌心相对,来回使劲摩挲几下,舒舒坦坦地吃饱喝足了。
碌碡被阳婆晒得滚烫,烙得爷沟蛋子疼。爷脱鞋,款款个磕出鞋碗里的干耥土,把鞋往沟子底下一塞,便包了一支野鸡大腿样的旱烟棒棒,对着刮白刮白的山梁吧嗒吧嗒抽。
把碗舔干净!——你阿门弄的,暂把碗弄得像个猪食槽一样。爷看着我的碗,斜着眼骂将开了,山羊胡子在白剌剌的日头下晃,就像屲上的缨缨草。阳婆晒得爷心上贼泼烦。
粘在碗帮上的馓饭用筷子豁不净,厚厚的像一层糨子。我双手捧碗,勾头展舌,学着爷的样子舔。尕狗学大狗拉粪,功夫不到,整不攒劲,只在碗里划拉了一些深深浅浅的绺绺道道,头发眉毛脸蛋子上都是饭糊糊,和汗褟子上的油汗板板一起,在毒日头下放着煜煜的光。鼻尖下巴上粘的糊糊最多,人舌头没狗舌头那样长而伶俐,只得用满是垢痂的指头刮下来再唆到嘴里。
——唉,你个泡蛋娃娃,吃屎都没人给你拉。爷叹口气,劈手夺过我的碗,伸出舌头三下五除二就拾掇干散了。
兀些年成,娃娃大人都得舔碗。娃娃大人吃馍馍时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生怕碎渣渣掉了,掉到地上碎屑一定要拾起来吃上。不吃有罪孽哩,哪怕你蹲在粪堆上吃也不能破这个例。
逢年过节,也会偶尔啃点猪骨头。一家老小就把上面的一点点筋筋串串又剔又刮,吧唧吧唧地唆来舔去舍不得给狗啃,在煮萝卜菜的时候还一遍又一遍地熬。谁家里来了亲戚,抬承地很了才吃顿甜饭。各家都有一个只能装一碗清油的尕瓷坛坛,供先人一样放在灶板的最高处。掌勺婆娘用筷头子蘸点生清油,在锅里涮几下,算是甜饭了。罢了还要伸出舌头,在坛坛口上舔几下,在筷头子上唆几下。谁家的媳妇子不小心撅折筷子打碎碗,或是撒点米扬点面,会被公公婆婆吊在嘴上骂半年。
庄子上人少,狗咬得紧,多时候是亲戚逛来了,亲戚一来要留下用饭的,不吃饭就不走。吃饭时一听到狗咬,爷立马紧张得脸抽搐,像要来土匪一样。过腊月八时,家里破天荒做了半脸盆洋芋菜合儿,刚端上炕桌子,狗就鬼哭狼嚎地咬开了。爷喊着我的小名儿叫赶紧赶紧栓大门。还没找到顶门杠,我外爷已经高声大嗓地进了庄。爷急了,端起脸盆就往毡底下塞,那只馋嘴的老猫闻着了味,朝着破毛毡底下吱喵吱喵直叫唤。外爷是个大心肝人,好开玩笑日弄人,就装作啥都没看着,一上炕就噗通一沟子端端个坐在藏了脸盆的那块破毡上。还一遍又一遍地问爷,毡底下啥东西垫得人沟蛋子疼,弄得一家老小脸红耳赤好不尴尬。
我和爷放羊回来,饿得前心贴后背。端起案板上的熟面就往嘴里刨,吃得急呛到了气管里,咳得昏天暗地,噗哧哧吹得熟面纷纷扬扬。爷掰开我的牙关子,一大洋瓷碗凉水灌下去,我才缓过气。可惜熟面扬到了灶头跟前的一堆麦衣里面,没办法扫起来吃,糟蹋了多半碗。爷惋惜地看着麦衣堆里的熟面,讲一个稀巴烂的故经。说六零年冬道里,下了一鸡爪子薄的雪,一个饿背扇的要馍馍客趴在地里找烂洋芋。不知谁丢下的一团苞谷面饼子,硬邦邦地横在雪上,便赶紧拾到破碗里。生怕别人发现来寻,就偷偷躲在地埂子根里慌慌张张啃,啃完了缓攒劲了,才觉得嘴里的味道很不对,——嗷吆吆,兀是一泡冻硬了的屎!那泡屎就救了要馍馍客的命!爷说的有眉有眼,俨然吃过屎的人就是他自个。爷说娃娃你没挨过饿,屎难吃田难种,阳婆这么个晒,麻达大着哩,过日子实实个要细详哩。爷说着说着舌头根子就有些硬了。
阿门要吃屎哩着?——我弱弱地问。
噫,你这楞棒,吃屎都没人给你拉!——爷端地是心疼得有些愤愤然了。
绿了骆驼蓬,老了菰子蔓,逝者如斯夫。
二
谷雨时节,天朗润起来,大片大片的阳光,穿行在麦苗和豆秧之间。
一墩墩的草瓜儿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淡紫的花从细长的叶丛中羞涩地伸开五个瓣,如空谷中幽幽的兰;一簇簇的打碗花,衬着狭小的叶片,仰着无数绯红的粉嘟嘟的小脑袋,开出莫名的娇柔;一坨坨的骆驼蓬、麻苦蕖、车前子、茨蓬……还有那些有名无名的野草野花,伸直了小蛮腰,抡开了胳膊腿儿;草尖上橙色的瓢虫,蚕豆花般的粉蝶,崖畔上橘黄的火食稼、桃红胸部的蜡嘴儿、善叫的麻嘹子、头上长了翎子的啄木鸟……用翅膀张开了春天。
榆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榆钱,天边偶尔有了隐隐的雷声。母亲从集上抓回一只大耳朵大肚子的 “狮子头”猪娃。这种猪腿短肚大,肥肉多瘦肉少,用洋芋和着麦麸,攒足劲喂上七八个月,杀翻后,割下一拃厚的背皮,能炼下来多半缸清汪汪的猪油。一家老小嘴上印着油圈圈,在庄子上就有了炫头,那可是猪圈里养骆驼——突出啊。
从这一天开始,娃娃们便有了新的盼头,单等着到过年时饕餮肥肥的猪肉了。云起云落,花开花谢。二十四节气就像爷甩开的泥脚片子,一步不停地跨过粉的杏花黄的麦穗。娃娃们还觉得时间过的太慢,盼星星盼月亮往腊月里熬。
腊月里了。慵懒寂静了大半个冬天的庄子,突然睡醒了,打个大大的喷嚏,忽地一下子哄伙起来了。日头暖融融像个裹着大红头巾的女子,温情脉脉地探着妩媚的脸盘子。缕缕炊烟,声声猪叫,村庄里便飘出了烫猪的腥荤味。
除了婚丧嫁娶贺寿做满月,杀年猪就成了阳洼人家四季里最隆重的节日。按照老辈的规矩,杀一只猪要来一庄子吃肉的人,一个猪脖子上的五花肉还不够招呼,破费不小。但阳洼里人实诚,谁家的人没来,还要装上一大老碗炒地油汪汪的猪肉片子和血馍馍,端到没来的人家里去。当然还碗的人也晓得投桃报李,绝不会拿空碗来。
奶手握剪刀,坐在窑门上,裁剪着红红绿绿的迎春的花儿雀儿;爷整完羊圈,将个土院子拾掇地净得能擀成长面。一群七八岁的毛孩子早早就等在灶头边,几个婶婶把两大锅水烧得滚烫。爷将杀猪刀、扫毛刀、剔骨刀磨得雪片也快,泄出道道森森的银光。
几个力大的男人撸起袖子,抓住猪孤拐,三锤两帮子就把那嗷嗷乱叫、踢脚撂腿的年猪压在炕桌上。爷接过杀猪刀,面朝东方念念有词。一转身,猛地用刀背在猪前腔子上一砸,一翻腕杀猪刀噗嗤一下戳进了猪喉咙,猪立刻发出狮吼龙吟般的惨叫。咣当一声,撒了盐的盛血脸盆就塞了过去,殷红的猪血泼喇喇顺着刀柄喷出来。不到半袋烟功夫,猪只剩下断断续续浑浊不清的哼哈声了。躲在屋子里的娃娃们便愈发兴奋了。——听到猪叫,就知道快有肉吃了。
一大背篼蒿柴杆子早将铁皮油桶烤得发烫,盛了半桶滚烫的开水,冒着腾腾热气。男人们抓住猪蹄上上下下地烫,待到脱下毛来的时候,把猪往烂耱上一横,便七手八脚地拔毛。少顷,黑黝黝的胖猪变得白溜溜的。娃娃们飞快而细心的将猪毛猪鬃收藏起来,货郎们转到庄上时,会换上几串鞭炮,单等年三十晚上给先人烧纸钱的时候燃放。
爷和几个把式开始对挂在架上的猪开膛破肚。我们专注地瞅着猪的两腿之间,蓄势待发,眼巴巴的等着抢猪尿泡。
“赶紧拿球子上玩去!龟孙子。”爷一刀旋下猪尿泡,扔给了一帮脏兮兮的娃。娃们一哄而上,像野狗抢骨头,嗷嗷乱叫,手忙脚乱。手脚麻利地娃立刻把猪尿泡里的尿倒掉,掺不上手的就捧几把干耥土,让最大的孩子把猪尿泡放在耥土里呲牙咧嘴地用脚揉,厚厚的尿泡便渐渐变薄。一帮子碎娃娃攒足了劲把猪尿泡吹了揉,揉了吹,才从拳头大吹到足球大,便赶紧找点麻绳子扎紧尿泡口。最大的孩子便把尿泡抛向高高的空中,大大小小的娃娃就像透圈的蛮骡子发情的尕叫驴,大呼小叫地围着猪尿泡转,或踢或投或拍或打,激情飞扬,野性勃勃。会打毛弹的娃娃一边拍着猪尿泡一遍念着顺口溜——打毛弹,绊袖子,你妈养了个头顺子,会爬了,会走了,你妈的肚子里可有了……这一日,欢呼声,哭闹声,合着庄子里狗的乱吠,鸦鹊的呱躁,公鸡的叫鸣母鸡的拍翅声,让孤寂的山村人气陡增,好不热闹。踢来踢去,娃娃们踢厌烦了,或是将猪尿泡踢破了,皱巴巴的猪尿泡便自然成了狗儿猫儿的盘中餐了。俗话说,猪尿泡打人骚气难闻,狗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这纯属妄言,编这些说辞的人,真是麻袋里装猪——不知黑白公母,哪晓得娃儿狗儿猫儿的快活?
金乌西坠,暮霭沉沉。山村腊月寒冷的夜寂寥而苍茫。
煤油灯下,爷拿火签子将炉子捅了一遍又一遍。爷说火是婆娘,越捅越旺,炉膛里的炭火便旺得煌朗朗响。女人们低着眉自顾自拉鞋底绣袜垫,男人们熬了酽酽的罐罐茶,谝着麦子豆子糜茬子荞茬子,谝着人老五辈的陈谷子烂麻子。在浓浓的旱烟味中,在幽幽的野狐精瓜女婿的故经里,吃得肚皮鼓圆的娃们,嘴上印着个油圈圈,倚在爷爷叔叔的怀里,早已进入梦乡下四川割麦子去了,狠狠地磨着牙,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淌着涎水,都成了属猪的——能吃能睡。
三
黄昏,有零星的雪片子扬起来。白日头悬悬个挂在沟脑上,没精打采地像肥婆娘的一爿大屁股,闪着幽幽的光,苍白的光。
游走的西北风,吹着尖利的哨子,卷起一团团燎眉子蒿。
爷穿光板子老羊皮袄,戴狗皮帽子,帽耳刮子耷拉耷拉地摆。筒着双手抱个拾粪叉子,背个烂茬茬背篼,头缩到皮袄领豁里,像只驮着壳的龟,沿着地埂低着头扑踏扑踏走。——爷拾粪盘光景着哩。
爷解放前念过初小,识得几个枸杞字。五八年,爷力搏正圆实,到岷县去改洮河。爷尕大算个秀才,会拉皮尺会给土收方,露了点锋芒,被派到兰州学了一年水利技术,分到了渭源的打井队,领着工资吃着皇粮穿着四个兜兜的干部服。爷没福,天天惦着屋里的奶还有一大帮娃。六零年,爷心急得坐不住,日急慌忙地往家里跑。到梁头上看见一堆新坟,爷以为埋的就是奶,腿就软软个拾不起来了。耱到屋里看见奶还在,娃娃们饿得头耷拉,幸好没一个咽气的,爷一凄惶,再没去渭源。爷又成了农业社里的人。
爷算盘噼里啪啦打得利索,便做了队里的记工员。生产队的洋芋籽放在爷庄里的上窑里,窑门上挂了锁,窑门顶上有个透气的天窗眼。爷饿得睡不着,找个长竹竿,一端绑个尖铁丝,爬上梯子扎出来半篮篮洋芋籽,放在炕眼里烧给一家老小吃。没过夜就被生产队长发现了,说宁吃屎不吃籽,你这是要让队里人都断子绝孙哩。爷立马就贬成了队里的羊户长(方言,羊倌)。
爷的羊户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那圈羊伴着爷,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绵绵不绝。一直到1970年队里的羊分到各家各户,从此,爷放羊的活结束。80年实行单干了,各干各,没耽搁。爹和几个叔年轻,爷放心不下,依然当这屋里的掌柜的,起早贪黑,不得消停,拼了老命务庄稼。
粪是庄稼的奶水。粪金贵,拾粪的人就多,没粪可拾。爷人机骨,有经验,知道小路旁,地埂子下面,隐蔽处的铁蒿丛里,芨芨草墩边,人粪多容易拾;大路上、场上或是地头上,肯定找不到粪的;走田地、走屲上的小路上,容易找到驴粪狗粪。爷每天早晚顺着这些路径,睁大眼睛伸长脖子,逡巡着每一个角落,发现一泡粪,就像走夜路碰见了银锞子,欢喜得不能言传。拾上一老茬茬背篼的粪,爷心里喝了浆水吃了酸菜一样,立马舒坦了。爷有时候太乏了,睡下听不见鸡叫鸣就起迟了,庄上的张跛子瞌睡少,早光顾了那些资源丰富的地方。爷不死心重蹈覆辙,只能一无所见,空斗而归。爷肠子里便像灌了羊油一样,会腻达达地难受半早上。
爷卸了驴扛着犁在路上走,那只麻身子白鼻梁的老骟驴突然撅起尾巴拉下了一泡热气腾腾的粪。爷没背背篼,怕走在后头的张跛子拾了去,手足无措,着急得很,急中生智伸出双手捧上几捧土盖住了驴粪。回到家里,顾不得喝茶吃馍馍,拿了拾粪叉子赶紧去抢。张跛子已经跛足先登,欢天喜地地拾了那泡驴粪正两腿一趔一趔地往自家粪堆边走呢。爷人性子硬扎,开头便亮亮豁豁一句你个驴日下的,张跛子也不绵善,不是饶爷的孙子,认粪不认人,也直戳戳对了一句相同的话。爷和张跛子尕的时候一达往牛把子里灌过土,是关系不错的老联手,只因为一泡驴粪,两人从饭罢骂到了晌午,谁都拉不开,真是粪堆前骂仗——要往死(屎)里整哩。饭罢都过了,要下地干活了,两人还觉得日娘倒老子地没骂舒坦,便都朝天上地下呸呸呸吐了无数口唾沫,才像两头凯旋的老羝羊一样,仰着黝黑的脸往屋里走,后板颈上的筋还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爷喜欢冬天。冬道里,狗就不栓了,母狗还会勾引来别的庄子上的公狗,旁若无人的在野地里乱骚情,羊和驴吆到了野屲上自己寻草撂蹦子,猪拱开圈门四处拉撒各处乱窜,拉粪的畜生多拾粪的机遇就不少。下点雪,张跛子腿就疼得下不了炕,再也没有人和爷顶着寒风在荒野里抢大粪。爷便早上在家里捣罐罐茶缓人,傍晚出去抓住机遇阔阔气气拾半背篼粪,从未悻悻而归过。
奶走了,十年纸都烧过了。爷无聊,觉得日子很是漫长,和自己同岁的老汉老婆子差不多死球光了,阎王爷就是不收爷。爷老颠董了。看着天上的雪片子扬,躺着躺着就翻起来,倒腾出拾粪叉子和烂背篼,套上光板子皮袄,出了门沿地埂子根里扑踏扑踏走。但地里连点粪渣渣都没有,只有被老北风扯成一绺绺的地膜,白花花地像引魂幡一样在四处招摇。
爷叹气。爷也晓不得,肩上的粪背篼背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拾了多少人粪羊粪驴粪蛋。爷理不出头绪,觉得自己很是孽障,便有些惶惶然,放了粪背篼,蹴在地旮旯里望着涝坝沿上那棵歪脖子老榆树张着嘴发着呆。树无语,对着爷瓜丢丢地看。爷说,你个鳖孙,打从爷穿开裆裤记起事,你就一直长在这达哩,这回阿们就认不得爷了。
作者简介

李进堂,笔名云山,网名云山猫。定西市安定区人,喜欢新闻、文学,从事过教师,《西部商报》定西站记者等工作,函授西北新闻刋授学院。曾经是甘电台、甘农报等报刊的特约通讯员。在《陇苗》、《黄土地》、《百花园》等刋物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民间故事等文章。
特别声明:所有资讯或言论仅代表发布者个人意见,乐多体育仅提供发布平台,信息内容请自行判断。
- 特别声明:本站所有直播和视频均来自互联网,本站不从事任何经营业务,仅为体育爱好者提供免费赛事数据服务。备案号:苏ICP备2020049342号广告合作@huzhan6688:QQ:95498723